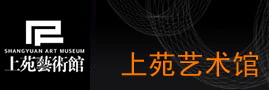|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70一代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对当代青年的影响与渗透,并从作为创作主体的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的创作作品来分析,这些审美趣味是如何发生转化的。主要涉及到的问题是:通过非政治的方式对后殖民主义的进行的文化反抗、人与欲望身体之间的矛盾与欲望的释放、KAWAYII美学与卡通绘画流行的分析、对机械美感和暴力美学的崇拜、酷儿主义之下的男权和女权主义。
关键词:70一代、趣味转向、贱文化、身体欲望、卡通、酷
这是一个价值转换的过渡期,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大众的道德经验和审美意识从集权压抑转为自我发展,并引发了巨大的内在的转变。作为过渡中的一代,70年代人的内部产生分化,并充满矛盾。能够坚守“个人奋斗”,争取个人成功,按照社会一般规律生活的人,是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成年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在经济快速上升时期的价值该是——“认真”、“忍耐”、“勤奋”。他们如果被称为主流的“靠谱青年”,那么,另外的一群,是拒绝崇高,寻求另类,随时随性改变人生路线,过审美化生活的人,则可以被称为“不靠谱青年”。他们代表另一种价值观——“消解认真”、“不再忍耐”, 这是社会从产业社会转型到消费社会后的价值形态。“不靠谱青年”不肯面对现实,他们退学、学画、留学,靠家里、靠天分、凭感觉,过着想当然的生活。从代群之间的差异比较来看,“不靠谱青年”则可以称为是70年代精神症候的典型代表。
“不靠谱青年”多半是外表灰暗,貌似老实木讷,实则内心闷骚花哨,无时不刻不是陷入到自我矛盾之中的一群。他们因为有理想而显得过于沉重,同时又厌倦他们所具有的理想和沉重,企图轻浮,又不太甘于堕落。他们在不同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和文化层面中选择,永远无法得到坚实可依的支点。他们随时打算放弃自己的立场,因为教育经历里发生太多立场转换,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值得信任和可坚持的。他们随时准备接受再教育,再改造,一切都可以推翻重来,但很难形成内心坚信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从小到大无处不是错乱,所以不稳定成了他们最稳定的常态。
法国社会文化批评家彼埃尔·波德埃(Pierre Bourdieu)认为,艺术趣味的差别和社会等级的区分有现实联系和历史渊源。艺术欣赏并不是一种禀性趣味,而是一种文化解码行为,它要求解码者先得掌握编码的秘密才行。主流美学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感知方式,掌握解释密码的人控制着知识话语权,高等文化人的身份也来自于此。整个历史之中都贯穿着不同社会阶级对“正当趣味”的争夺。趣味比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更需要在反面否定中获取确立性。趣味也许首先就是一种“厌恶”, 一种出于对他人趣味的恐惧和出自肺腑的不宽容所引起的厌恶。每种趣味都觉得只有自己才是自然的,于是便将其它的趣味斥之为不自然和邪恶乖张。审美的不宽容可以是充满暴力的。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反感,可以说是阶级之间的最顽固的壁障。那么,以此反推,如果某种新趣味让习惯于即成趣味的人群感觉到愤怒的话,那么,它有可能是审美革命、自由感知的开始。只要排除固有偏见和道德训诲的批评观点,本着实践精神,认真的对待研究对像,我们就可以看到,审美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断流进变化的过程。如果说“不靠谱青年”的思维方式会对审美经验有什么新的突破的话,则在于他们本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心态,勇于戳破人性种种的痛与恶,敢于面对和承认自己的弱点缺陷,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身份。70一代区别于前代,具有开端性和革命性的审美趣味,归纳起来有四种,犯贱、发骚、装嫩与扮酷。它们都是非自然的感觉,是对人为造作感觉的偏爱,是一种70年代人所集体共享的、秘密的新的感知力。这些审美趣味已经作为一种身份标志,分别在渗透在装扮、行为、态度、语言等生活方式里,艺术作品也是它的一个表现方式。
一、犯贱——弱者的娱乐化反抗
“你说谁是贱人?这里都是贱人。”——《大话西游》
2000年开始大规模流行的韩国流氓兔和巧克力贱兔,成为犯贱美学的先锋,主角是以厕所刷和坐便器为标志的流氓兔。这是一个无恶不做,对真善美大肆糟蹋破坏,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流氓英雄”形象。巧克力贱兔则是毫无创见的步流氓兔后尘,屡战屡败,遭遇惨烈的搞笑形象。贱兔表演性质的自我作践与失败,显得更加具有审美内涵。清华学生对芙蓉姐姐的夸张性的欣赏与追捧,与此有一脉相承的心理结构。作为一种文化消费,香港无厘头烂片、康熙来了、吴宗宪与大小S的娱乐节目,都是充分利用互相折磨与自我折磨的快感,打造出来的消费产品。他们使一切严肃的东西不再严肃,通过对精英文化践踏和亵渎释来放快感。他们先通过对自我的贬低与嘲讽,进而贬低和嘲讽他人,践踏尊严为代价,建立自己的逻辑和秩序,从而获得娱乐大众的效果。这种趣味被大多数的70年代以前的中年人所唾弃、排斥,在青年人中却已非常广泛和固执的深入人心。他们对自轻自贱身体力行,比如当下流行的互为宠物的游戏。从趣味所产生的排它性和压迫性来说,70一代基确立了对贱趣味欣赏的转型,并以此来确立自己。视觉艺术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产生的一系列连锁的现像。从艺术形式来讲,是对错误、廉价和粗糙的热情拥抱,而非掩饰或消除,比如手机或网络的低象素数码图片,过期的胶片和相纸的使用,LOMO的虚焦与暗角,“坏画”的低技术含量化,装置材料垃圾化与未完成化等等。内容则体现在无聊化、游戏化、娱乐化和草根化。
徐震是典型具有贱趣味的青年艺术家,作品《喊》是几个无聊青年,在类似闹市区地铁口的人流众多的地方,毫无来由的大叫一声,并同时拍下所有中了圈套、回头观看群众的木然表情。一群无聊的人在拿同样无聊的大众开涮。艺术此时被虚化为都市小混混用恶搞来打发时间的空洞、无聊的游戏。《12秒91》利用了周星驰《功夫》里面的意像,一个翻制的等大的坦克,炮筒弯曲下垂,钢铁车身上布满了入铁三分的掌印脚印,那是脆弱的血肉之躯和现代化杀人武器的狂欢式的较量。《彩虹》是自虐般的不停抽打自己的裸露后背,用疼痛抖动换取漂亮的一抹鲜红。阳江青年郑国谷更是深得“贱趣味”精髓,作品《大减价》模仿广州街头甩货时的手写告示,上面用各种扎眼颜色生猛的书写着“狂减、劲减,一减再减”,“爱子吸毒,老婆走佬,女儿去癫”,“生活灭望,彻底清仓”。他试图把所有的一切打回原形,在货声嘶力竭的叫卖中,在游戏快感的掩护下,戳穿了市侩的商业骗局和廉价的底层生活的本来面目,同时以粗俗恶拙的街头广告作为高雅的书法艺术的颠覆。
曹斐是78年出生的女艺术,她的实验戏剧《珠三角枭雄传》通过民间野史、互联网传说、时下热点为主题,把目光落在二奶、民工、乞丐、木咀美、酸中山、杂耍者、发廊妹、卖盗版光盘的人等一系列非正当职业者身上。全部用当地方言、俚语、脏话、粗口恶狠狠的念白,把大街上店铺放的粗俗的流行歌曲作为配乐,通过戏仿、夸张、篡改的方法组织成了一场表现珠三角鲜活生活现场的闹剧。在这种花哨的娱乐化的形式下,是对这种失控的荒诞,另类的秩序进行一种批判和反思。《三元里》中对晨练老人背影偷拍的快速倒放和摆拍的白领职员模仿名牌狗的《Rabid dog》图片,也充满了调侃的贱趣味气质。
76年出生的秦琦,在油画《只要你别伤害我,我什么可以都给你》中,一堆凌乱的家什,一个不太强大的对手,穿黑色西服的男主角面对突如其来的劫持,自茧双手,乖乖的趴在双人床上。在习惯性接受不公正境遇和逆来顺受的屈辱之中,对无助、委屈、尴尬与蹂躏的反抗变得毫无必要,不如加入犬儒主义玩世不恭的游戏之中。另一张是画家本人,穿着肥大的男式蓝印花内裤和灰蓝色夹克。滑稽的是,他一头栽进床下的颜色花哨的铁痰盂中去。在一瞬间,被动的受虐转化为主动的自虐与自贱,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快感。
杨福东的图片作品《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中,那个站在马路中央,头破血流,高举板砖,却找不到人拼命的那个邋遢认真的西服白领,也利用了贱趣味来解析调侃小知识分子无用无能的内心创伤与反抗。而陈晓云的录像作品《插座人》,是一个长相很二的眼镜男,身上缠绕着很多电线和插销板。他时而在城市雨后的烂泥工地里爬行,时而白日梦般的在地铁通道的地面上呆坐,遭到周围人的旁观、冷眼、嘲笑,最后拳打脚踢的待遇,体现了在电子时代中,都市化生活的孤独与苦涩,是青年的个人内心的独白。
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者斯考特(James C. Scott)的研究了下层群体对抗权力方式。他认为低调斗争有能成为供君王逗乐的丑角表演,相对无权群体的平平常常的武器是不合作、放赖、阳奉阴违、小偷小摸、装痴卖傻、流言蜚语、放火破坏等等。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受制群体,也包括极权和威权社会中,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斯考特更关心日常生活表现,尤其是那些心照不宣的表演性(他称之为“公开语本”)、创造性潜台词(他称之为“隐蔽语本”)和非政治的政治(他称之为“外线政治”)。当代艺术中对“贱”文化的利用,是从反崇高并直接嘲笑体制的政治波普,跨入日常生活的超越羞耻感的自我嘲讽,是70年代独特的娱乐精神的体验。“贱”文化趣味的力量,源于对大众娱乐的欲望,这是一种宁要世俗不要理想,宁要欲望不要情怀,宁要宣泄不要升华的艺术,一种反美学、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的解构话语方式。它又并不只是简单的反文化,与平庸恶俗的与娱乐节目和流行文化同流合污,而是把生活作为一种源源不断的新的感知力的源泉加以利用,通过表演、狂欢、疯癫、自我作践等方法,以非意识形态的面貌,进行对后集权社会的反抗。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变相的和隐蔽的精英主义,一种下里巴人的阳春白雪。在主流艺术守旧、官样、反动、千篇一律的状况下,以肉身的天赋、敏感和创造力,攻打出的一个新的自由选择、表达反抗的出口。
二、发骚——欲望身体的内爆
出于对虚伪和做作深恶痛极,发骚更显得具有媚俗和自娱的职业道德。发骚表现了一种情欲上的被压抑了的骚动的不可言说的快,很象是“力比多”的庸俗说法。可以被解释为去除心智能力后,与生理本能相联系的精神性的内部驱动力量。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在消费文化中,如何处理自我与欲望身体的关系。德里克“后革命”的说法就是将政治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校园革命——青年学生力比多的发泄。演艺娱乐圈对性感撩拨的追求成了发骚的诞生地,但是发骚已经远远超越了性感的概念,是一种未能尽言的男女不限的引诱和挑逗。往往是外表木讷、老实的男人发骚,更具有娱乐力量。由70年代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美女作家,都是利用了此种趣味来撩拨大众的道德底限。在视觉作品的创作中,如果进入精神分析的方法,则是一种对情欲未满的宣泄。比如沈娜画的那些胸部键硕、眼波飞舞、小腿细脚的表达出强烈欲求不满的浪荡女人形像,是发骚趣味的典型代表。也包括对老月份牌的热衷与返潮,形成了一种“新艳俗”的追求。所谓“新艳俗”不是农民品位的艳俗,而是小资白领的洛可可式的享乐主义的艳俗。
如果说发骚有等级和境界之分,那么闷骚型,则代表了70一代心理特征的最高境界。闷骚,假性贬义词,指表面上矜持沉默,骨子里如火山爆发的人。压抑隐忍的“闷”具有表里不一的矛盾性,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本质依然是“骚”。闷骚是一种迂回的表演,因含蓄而上升了一个境界,是一种假正经和低调的放肆。它蛰伏在人的体内,假寐、积蓄、含而不露、欲说还休,时机一旦成熟,就立刻苏醒,继而惊世骇俗。家庭伦理、学校教育和社会体制,是让70一代自我压抑的主要因素,越是想表现得优秀便越享受到这种道德伦理和体制上的压抑。他们从小就会纷纷放弃自己的天性爱好,重新按照外来的价值观塑造自己,比如投奔应试教育。他们价值观是扭曲的,成绩或金钱高于一切,很多更重要的因素在价值观中消失了。但是原始内在的欲望和表达的力量并不会在外界的压力下而丧失,比如信仰、人性、沟通,甚至性欲,它只是以更为隐蔽的形式进行了其他的转化。由于被压抑的东西往往是不能获得正常的表达的变态的,焦躁的,扭曲的,疯狂的,不能公开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以极端的自虐的形式出现。比如赵能智的油画就是最典型的“闷骚”写照,在幽暗的背景上,扑面而来的一张憋红了的大脸,浮现着一种心里有话却无法讲出的难受的表情。“她/他”被无来由的外在巨大的力量所压抑,而内在生命力量的冲撞而蠢蠢欲动。由于迫不得已的现实,“她/他”不得不拼命隐忍着、吞咽着内心撕裂和焦躁的痛苦。李大方和谢南星的油画,骨子里也闷骚的。李大方表面上波澜不惊的画面把人带入神秘、惊栗、恐惧的心理世界。平静的夜晚对面大楼里正泛着几缕诡异的灯光,荒蛮的原野里闪动着令人不安的零星篝火,人物稍纵既逝的隐忍表情和想要干点什么跃跃欲试的姿态,一切都处于千钧一发的惊恐之中。闷骚的高级境界既是撩拨。谢南星《令人讨厌的寓言图像》是最为极致的闷骚表现,一个人在徒空四壁的封闭空间里,噩梦一样的用刀片切割自己的身体和生殖器,鲜血直流。尹朝阳的《神话系列》中,一个被过剩的力比多所驱使的人,为了压抑心头蠢蠢欲动的邪恶欲望,不断的苦役般的重复着西西弗寓言中的劳作。
在对欲望的个人压抑下掩藏着强大的自我张扬的动力,这就是“亮骚”。亮骚是大张旗鼓的性感。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摆谱”、“卖弄”或“臭美”。寻求“炫耀”,在动物性中是吸引异性的本能,在人类社会里演变成获得社会的认可和他人的敬佩的心理需求。人们在自恋文化中可以获得虚幻的满足,可以被看为对社会压抑的解救途径,社会的“减压阀”或“黏合剂”。对自我的关注,自拍,自传,自画像,表演性的展现,身体的觉醒,都是自恋意识的主要表现。一群新的人格类型开始出现,网络上出现的大量自拍和全民博克日记,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等,都因其大胆豪迈的我型我SHOW而成为代表。喜欢自拍并在网上贴照片的动力,是源自内心的孤独和强烈的表现欲望。自恋是个体在压抑沉闷的环境中,建立自尊自信的一种方式。自恋人格又称“帕索斯症”,是希腊神话中,为了追寻自己的倒影,投水身亡的那株摇曳生姿的水仙。症状被描述为“过分的自我意识”、“对于健康的持久的不安”、“恐惧老化”、“对于老化徵兆的极度敏感”、“试图出卖自我,好像是一种商品”、“渴望情感体验”、“沉浸于永远年轻与充满活力的幻想”。比如在杨福东的录像作品《陌生天堂》中,男主角有反复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怪癖。彭东会把《我与999个网友》的自拍铺天盖地的罗列,李威的画《W先生的现实生活》系列表达了对自己的身体和光线的移动所产生的变化的敏感,丁洁则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自拍照片处理成四方连续的图案,都是自恋症状的表现。忻海洲的画里脆弱而紧张,充满忧虑的,顾镜自怜的大眼睛。张小涛的油画中,把透过玻璃杯自拍的变形的头像放进彩色的避孕套里。他对使用过了的透明巨大的避孕套,金鱼,以及周围暗红色不明液体痕迹的描绘,是在对宣泄过了的性欲和性能力进行事后的张扬和炫耀。女艺术家陈羚羊的自恋则体现在对女性所独享的月经体验的释放,《十二月花》的图片作品也采用了自拍的方法,她用古典的镜子折射的自己月经期间鲜血淋漓的生殖器,并配合当月开放的花朵,组成一幅神秘深邃的画面。照片上,裸露之处诱惑着他人的窥视,而恶心的经血又把人拒于千里之外。刘韡用腿毛男的蜷曲的毛腿照片组成了云烟漫灭、远近错落的黑白山水画。腿毛这个粗俗鄙陋,不可亵玩焉的隐秘身体的性感细节,也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一个具有高雅意境的欣赏物。
三、装嫩——彼得·潘的永无乡之梦
最小的70年代的人也已经有二十大几,他们多半抱着“还没来得及放肆,就已经青春不再”的遗憾心态,直向三十而立奔去。由于心理上的不成熟和对家庭的依赖性,使其中的一部分人下意识的拒绝长大,宁愿沉醉于白日梦般的幻想,患上“彼得·潘综合症”。 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ie)笔下的彼得·潘,生活在梦境一般的“永无乡”中,永远也不想长大。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不愿离开学校,不间断的尝试更高学历的考试,着装哈韩哈日,追捧KAWAII(日文“可爱”)美感。经过多年的浸泡,装嫩的美学趣味已经真正的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日常状态,不再具有像“贱趣味”那样的革命性和“骚趣味”那样的极端性。或者说它从一开始就不曾具有过文化意义的使命感和颠覆性。它在趣味上自成体系,另辟蹊径。虽然与所有的曾经的地产文化有所不同,但基本属于大众娱乐的泊来品,一种对青春期记忆的文化消费,一个日韩款的国际流行的时尚样式。卡通更像是一种形式,如同插图,连环画的类别属性划分。除了样式之外,它自身很难提供出一种新的思想资源和创造性因素。虽然它可以触及到很多问题,但依然只作为载体。内容上,它可以是柔情少女漫画、暴力的铁血漫画、色情的成人漫画,幽默的励志漫画等等。形式上,它即可以是手绘单勾,也可以是三维建模的。这就如同油画并不挑剔你是打算批判现实,还是超现实,也不在乎你是肤浅的庸俗甜蜜,还是深刻的痛苦不堪,它只是画种。卡通所提供价值在于可爱、甜美、清新、幼稚的趣味提示,而不在于卡通形像本身,经管那会因为专利权获得商业价值。不论是卡通的读者还是创作者,都以非常快的速度更替,就如同对儿童文学的消费,它更适合在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年龄阶段的文化消费产品,而不会成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虽然我们依然心甘情愿的患上“彼得·潘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生活终归会来找到你,并气急败坏的打碎梦幻。卡通绘画更像是“文人画”,只能做精妙趣味的高低品评而绝对不能分析,它能使人逃脱出现实空间,用暂时的舒缓,屏蔽掉整个社会。用《无间道》里的一句话讲,“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
在流动感和现实和虚幻的挣扎中,对KAWAII美感的利用,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依然在梦幻和梦醒的两维之间左右摇摆。卡通绘画因为具有强烈的模式化样式化的因素,又严重的脱离现实生活,不能够像真正的卡通漫画一样的进行长篇的连贯性的叙述,只能用单幅平涂的方式勉强抽像的表达一些概念化的感受。所以很难维持长久的兴趣,也少有余地进行长期的实验和自我创造。卡通在创造了形像之后,更需要的是一桢一桢画下去的耐心和定力,以及对整体叙事的架构和把握。但我看不到如火如荼的卡通绘画除了商业,终将会走向哪里。是“装嫩”的趣味而不是卡通的样式,作为一个泛亚洲化的大规模的趣味转化,依然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文化折射。有意思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内外矛盾的“装”,更在于表面上的“嫩”。由于先天所具有可爱甜美的趣味因素,卡通形像在艺术作品中经常以一种亚文化的姿态出现,以此来强化艺术语言上的对比。曹斐的《cosplayers》中,打扮成电子游戏中超级英雄的男女青年无一例外的生活在自己的梦境世界里。在日常的家居生活背景下,他们拂拭宝剑或是揽镜自抚,与正在烧菜的母亲或是翻报纸的爷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在俞洁的《白日梦》里,几团悬浮的软绵绵的云,内部透出橘黄色光亮,好像落山的太阳就藏在那里,一些纤细的小人影影绰绰的藏在云彩的皱折。这是一个臆想出来的充满安全感和温暖的乌托邦的梦幻世界。在《大玩偶》作品中,一只戳到天花板的绿色仙人掌的红色小球上顶着一个彩色柔软的棉布娃娃。幼稚与美好之伤总是夹杂了与现实生活不和谐的充满挫折感的生活体验,经常被用来作为作品表现的主题。与此相似的还有李颂华的作品《童话》一个小小的婴儿玩偶,步履艰难的背负着一个洁白羽毛搭建成的金字塔,而从地面的镜子来看,它正处于巨大金字塔的顶端。李继开的绘画作品里充满了卡通人物般的木讷形像,用纤细的闪电、受伤的玩偶、游戏般的射击和呕吐,造就一个敏感、灰色、沉默、伤感的内心世界。他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叙事风格摧毁一切美丽的表像,让观者直面成长过程中的痛苦与黑暗。与此不同的是,刘鼎用白色发亮的空胶囊组合而成的《蘑菇》,和用红色塑料亮钻拼集而成的《小人物的狂想》,提示了一种对小物件的过分的欣赏和喜爱,调转梦想与幻灭,对具有KAWAII和尖锐伤害气质的物品充满了恋物的情绪。反对深刻,只表达一种很浅层的快感,创造一种陌生化的喜悦,可以说是KAWAII滥觞的最主要原因。
四、扮酷——暗夜冷金属时代
经常可以看到,表情冷漠,举止成熟,略带不屑的高个青年,出于对社交的恐惧与不自信,他们更习惯少言寡语的表达方式。“酷”源自麦克卢汉用来解释冷热媒体时所用到的“cool”。在本质上,酷是一种与技术的融合和、去性别化的冷。支撑“酷趣味”转化的三种形式分别是:机械崇拜、暴力美学和酷儿主义。
对名牌、简约、冷金属质感,高科技的智能,机器美感的追求,成为扮酷的标志。因为都是灰色和冷的美感,机械崇拜和暴力美学经常掺和在一起,被大量的使用在3D游戏和科幻电影中,那些对未来太空和世界大站的描绘,是对科技进步的疯狂和崇拜。“Cyborg”,这个名词是Manfred Clynes与Nathan Kline于1960年所提出,指的是采用辅助的器械,来增强人类克服环境的能力,后来指有机和人工的系统存在于一个生物体上。假肢、假牙等这些人工器官,将人变成了Cyborg。在《终结者》、《机械战警》和《骇客帝国》中,Cyborg是机械入侵人体的交融物。这经常成为70一代艺术家的画面表现内容,比如张燕翔的那些变异的机械植物组合成的多媒体作品,朱海的油画中类似巨大鱼卵一样的金黄色怪物身上生长出金属框架,付晓东的《机械生活》则是把工厂拆迁的钢铁垃圾,处理成凌空生长的怪异而巨大的肮脏花朵。行为艺术家杨志超曾经把一条真正的金属尾巴移植到自己身上,长达一年之久。
“Cyborg”的概念可以扩大为城市,利用宽频网络建立虚拟城市“Cyborg City”。如同Google的3D地图,人可以通过非实体接触,仅通过电话线进行网络的沟通交流,虚拟既是真实。冯梦波的互动游戏作品《Q4U》则建立了一个这样虚拟的城市空间,并结合《CS》里的攻打经验,伺机埋伏,对虚拟的敌人进行猛烈攻击或者自己遭到血腥屠杀。这件作品还牵扯到“暴力美学”的概念,COOL的低调和零度情感,也同样适合于暴力美学。暴力美学以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为最高代表。在他的影片《低俗小说》和《杀死比尔》中,暴力被全面颠覆,成为了一个玩笑,一个日常的生活状态,一种唯美而残酷的镜像语言。他的影片里充满了无铺垫、突如其来的杀戮或死亡,拿那些无头尸体、斩断的肢体和车后坐上的血浆来说笑。暴力的存在除了娱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古墓丽影》和《CS》等3D游戏里不断重复强化的虚拟屠杀经验的快感下,其负面影响是对社会新闻的犯罪也表达出一种犬儒主义的麻木和冷漠,正应了《娱乐至死》中的担忧。史金淞是此种趣味的出色代表,从他的作品《冷兵器》是貌似耐克标志开刃弯刀,摩托罗拉标志外型的流星锤,还有奔驰标志似的飞镖。装置作品《刑具》则是把冷亮的不锈刚健身器材和电脑设备,改制成了只要稍一牵动,就会自动斩手、断腿、凌迟、截腰的自残凶器。UNMASK小组也是充满了未来气质的组合,他们的《6月20日》是一个巨大的不锈残破钢机器人,他发生了意外,摔在地上。碎裂的开口处可以看见精密的电路的结构,它的躯体开始融化,周围是粉红荧光的警戒线,可以看到从头部流出的金属血液组成了充满调侃意味的三个字——“失败了”。最具暴力美学特征是何岸和朗雪波的作品《180度》,他们把电影史上那个最长的强奸镜头中的截图画成了6张油画,在灯光昏暗的地下通道里,一个醉汉不停的殴打、辱骂和强奸一个妓女。这种对暴力的欣赏,粗糙、生硬,而且如此强烈,如同第一次抽烟的突兀感觉。
另外一个展现扮酷趣味的则是僭越性别观念的酷儿主义。“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男女两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理学统计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处在两性之间,他们的生理性别是不确定的。根本不存在像合法的性别身份这样的东西,而我们所理解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其实正是被社会制约的表演”。酷儿理论的核心就是取消社会第一、二、三性别的等级差别和压迫,使双性人、异性者、同性恋者也都获得平等地位和自由展现。“中性”趣味从以前被压抑被贬低的地位,成为被推崇的性别价值取向,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流行时尚,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和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受到了追捧和赞扬。女性主义运动带动了男性解放运动,后者在欧美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二者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促进着人类从旧的社会性别角色里解脱出来。男性解放运动鼓励男人自由的、按着自己的性情去生活,出现男性选美、男性美容,甚至于男性卖淫,多元的价值选择成为可能。在“超级女生”中,获得最高票数的李宇春则是以“阴柔和阳刚”两种魅力穿透了所有人的心,有一种纯洁的妖艳,率性的妩媚。同时,也可见中国的大众对于中性、另类美感的普遍接受,已经超乎想像的提前到来。蒋志的图片作品《尘世间/同体》拍摄了很多迷雾里具有雌雄同体气质的都市男女,需要仔细打量,才能从或妖艳或冷俊的外表下认出与之相反的性别。严程也在同时关心着同样的题材,《未可定义的青春》拍的是校园里的中性化状态。蒋志的Vidio作品《香平丽》则是拍摄变性男人做隆胸手术的全过程,其血腥和残酷的过程,实质是这个社会对男性性别规划巨大无形压抑的血泪控诉。与此一系列的《M+1,M-1》则是做了隆胸手术的男性舞蹈家,和做了乳腺癌割除的女舞蹈家的对比照片,把这种中性之美直接、尖锐的呈现在人们面前。除了人的社会性征外,性别在长时间的社会生活里,已经成为了一个趣味上的形容词,比如蕾丝、漂亮、阴柔,是女性化的,而方直、阳刚、坚硬,则是男性化的,儿童化,男女气质混合,雌雄同体的形容词,则是中性化的。“中性化”也可以是一种抽像的物质的美感,可以泛化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UNMASK小组做的《鸡尾酒杯》,是将常规玲珑的鸡尾酒杯轮廓嵌于一个透明实心圆柱玻璃当中,使传统鸡尾酒杯的脆弱视觉感和凝重手感并存,而更显中性的魅力。
四种具有颠覆性,反叛性的美学上的转向,有时候也是互相渗透在一起,水乳交融。经常一作品同时具有二、三种以上趣味,这些趣味都是贯穿在自我关注、去意识形态性、游戏性、娱乐性的“不靠谱青年”的审美之下,具有原则上的统一。同时,在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面前,艺术依然只是一个侧面呈现,显得多少有些软弱无力的苍白。但也正因为艺术的转化,而使现实得以存留。
(付晓东 艺术家 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