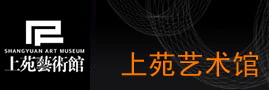|
程小蓓的记实性小说《无奈》之三、初识监狱
[2009-8-11 8:47:15]
程小蓓的记实性小说《无奈》之
三、初识监狱
1
那年夏天,蚊蝇最穷凶极恶的时候,我来到了蚊蝇密度最高的地方——西域城巷子监狱。
它在一条杂乱无章、泥泞不堪的城边小巷子尽头。一扇双开大铁门正对着巷子,大铁门关着,只开一扇小铁门,门内五步远的门卫岗亭里,立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大兵,表情冷酷、麻木。
我被告知入门前要叫“报告”,等待指示方可步入。首次进入这样的地方我感到惊恐和新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过了这道大门进入一条右边是提审室,左边是办公室、值班室的过道。安警们在左边的对外接待窗口,递交各种关押手续后,把我交由一女狱警。
在接待窗口的边上有一室内过道,入道前还要叫一声“报告”后,女狱警带我穿过走道进入一内院,院中有一排排平房垂直于我刚进的那排办公平房。女狱警一脸疲惫、公事公办的麻木。在我被带进囚室前,女狱警对我进行全身彻底的搜查,连乳罩下沿的那根造型塑料和一双皮凉鞋底部里的钢板(她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那里边竟有钢板)都一一剪开去除。
现在我清楚地、入骨三分地知道了:
在这儿你不可以有尊严,所有人的权力均被剥夺。
女狱警很重的开门声,进到了囚室里。囚室分里外两间,外间为放风间,半露天的,约有4×4平方米大,有自来水龙头,有碗柜在左内角,碗柜里整齐地排放着碗和杯。天花板上是一些10-20厘米宽的条形水泥方梁,梁上有七里香类的藤本植物。在右边的梁上一字排开地挂着衣物,挂得很有规律。我还注意到地上很干净,一尘不染。左边墙上有一条绳子,上挂约20—30条毛巾,一律如火车上看到列车员整理车厢时所折叠的那样:折成10×10厘米那么长宽。
进里间囚室的门是铁栅栏状的,在放风间能清楚地听到里间有一阵轻微的骚动声。由于到达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囚犯们都睡了,所以听到一阵木头床板与肢体的碰撞声。这时候狱警叫了一个姓田的“招集”(即犯人头)出来,一边说话一边开里面的第二道铁栅栏门。这道铁门与外面的那道铁门都靠右边对应着。在里间的左边有一比门宽一倍的铁栏杆窗户,窗上没有玻璃。我看见窗里一胖胖的、约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动作麻利地应声站起来下到门边。
狱警说:“是经济犯,我看过了,很干净。你再查查她的行李,安排一下。”说完将我交给里间的田芳招集,“咣当”,震耳欲聋的关门上锁声后消失了。
2
田芳招集接过我的行李抖抖捏捏时问我因何事而入?我告诉她因在公司的经营上出了问题。答毕,我看她面善便反问她:“你,何事?”
她只简单地说:“我是因为银行的事,被人害入此地。”语调低沉。
在我们俩简单的对话过程中,看见囚室里约有二十几人,大多都半支着上身看着我们。都很年轻,发出一些耳语气声。
看来田芳招集对我的印象还好,语气中透着平等、关照,使我忐忑不安的心情能平缓下来有闲观察一下周围和犯人们。
里间比外间长一些,约有5—6米,宽度是一样的。右边的门宽便是里间走道的宽度,走道的尽头是一由水泥砌起来的便器。看到它我不寒而粟。它让我想起,潘家柱从此监狱释放出去后,脸色铁青着给我说的:他被逼着用舌头打扫厕所的事情。一阵难以抑制的恶心袭来,我立刻紧闭双眼,求神保佑我千万不要遭此罪。
我小心翼翼地转过头来看左边一大排用水泥起脚、上铺木板、边镶角铁的通铺床,高约50厘米。里墙在高约3米的地方有一观察窗口,不是里面观察外面,而是外面有一观察走廊,看守每小时在上面巡视一次。从里面往外看能看到被铁栅栏划成条状的天空。有的人一进来就是几年,天天看到的就是这一方天空。
正当我灰灰地悲怜着自己时,被叫入睡。
女囚们一正一反交错着,如沙丁鱼般摆放在床铺上,由于七月的炎热,女囚们仅穿着胸罩、三角裤,几乎是赤条条的,一个紧挨一个。
田芳招集用命令的口气,在第十人的位置让出了不到一尺宽的地方来安排我躺下。
由于紧张的审讯持续了一天半宿,已近临晨,疲惫之极,倒头便睡。
一个噩梦还没做完,一阵强烈的广播喇叭声使我惊醒。
必须迅速起床。
刹那间,床板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单被子折成了军队那种棱角分明、方正的样式。女囚们训练有素地排列整齐,端坐在通铺上。
看守进来开了“放风门”,大家齐声高叫:“看守早晨好!”
而后,田芳招集报告昨晚平安无事。看守用眼睛在室内各处扫射一番,没看到不顺眼的地方。于是开门、出去、上锁。我们便有序地出去洗漱。
随着“严打”活动的进行,每天被关进来的犯人直线上升。最后这约20平米的囚室里竟多达三十几人。如暑假期间的火车厢,所不同的是没有看风景的窗户、没有可口的盒饭、没有尊严、没有希望、没有可以停靠的站台、没有可以保住的秘密、没有神秘的旅伴。
3
那年扬子到遥远的城市去读书,第一次放暑假,回从小养育她长大的爷爷、奶奶家。
那辆人满为患的火车,就是这样。三个人的座位上有五个以上的屁股,这是幸运的。更多的人在走道里、车箱的接头处站着。男男女女都紧贴在一起,没有了界限。晚上座椅底下会有两个以上的人钻进去睡觉。行李架上也有人爬上去,睡着了掉下来,砸在下面人的头上,就引来一阵咒骂声。最后是座背椅上,茶几上都垒满了人。如果车的顶棚上有钓子,恐怕也得挂上人。
吃饭、喝水、上厕所比登天还难。
扬子在座椅上靠窗最好的位置,这是从起点上车的好处。她左边也是一个执学生半票,从起点站上的小伙子。他们三天在一起的旅行没有说一句话,可有一种神秘的交流在他们之间进行。他的右手臂紧挨扬子的左手臂,他的右大腿紧挨扬子的左大腿,到疲困时,都扒在小茶几上睡了。扬子虽是极度的疲困,可脑子总因紧挨的小伙子而清醒着。
扬子感到了小伙子的手,在茶几上摸到了她的手。一阵电感。她没动,继续睡着的状态。不知想看事态如何发展还是渴望这种电感。小伙子轻轻的来回抚摸着这支被头压得麻木的手。当她想将麻木的手换一个轻松点的位置时,那支抚摸的手就触电般抽走。
这样,只要他认为扬子睡熟了,就会去抚摸她的手。不再有进一步的动作。他从没看扬子一眼,扬子也从没看他一眼。
神秘的旅伴。
这样苦不堪言的旅行,因有了这神秘的交流而变得有意思起来。最后到了扬子要下车的地方,从行李架上拿箱子时他才说了句:
“我帮你拿吧。”
于是扬子很放心地从窗口跳下车去,再接住他递给她的箱子。
车厢门从起点站开出后,到扬子下车就从没有开过。人们堵塞在车里也没法开,要是一开,人们肯定会像爆了的饺子馅一样从里面往外爆。人们都是从窗户上下的。
扬子没说谢谢,也没有回头再看他,就出站去了。
现在扬子呆的牢房,只要看守将风门一开,囚们就定像饺子馅一样爆出。
4
我第二次被捕后,从西域城监狱转移到平庄地区监狱。这里留给我的记忆将终身陪伴我。
平庄地区监狱坐落在离街市不远的一个小山包上,一条泥沙土路直通监狱。远远的,从吉普车的档风玻璃看出去,有两个水泥方柱立在路的尽头,上书“平庄地区监狱”。方柱的左右两边是炮楼,有真枪实弹的大兵和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雕堡上的那种探照灯立在上面。
穿过立柱和炮楼便是一排两层楼的平顶房,长约300米,正中是一扇密缝的大铁门,门的左侧是一排接见室,右侧是对外办公接待室等。
一名安警和我在车上,等他们到接待室办完手续后,有人在那扇大铁门上打开一道小门,将我塞进去。这道门进来容易出去难,它对我来说还特别昂贵。
进了这道门后,里面是一宽约10米,长150米左右的小天井,后勤部门都设在这天井的周边房子里,如火房、值班室、办公室、医务室等。
从值班室里出来一男看守,将我带来的所有物品打开,倒在天井的地上,一一查看,将硬物如头发卡子、手表、针线和长一尺的绳子(包括鞋带)等统统掏出来没收了,但没搜我的身。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是男的不便搜查。
之后,他带我进了天井中间的一个室内过道,用钥匙打开第二道铁门,我进到了一个大四方形院。中间的天井有100×50平方米,有喷水池、花台和四周围50厘米宽的排水沟,沟的外围是四排合拢相连、上下两层钢筋水泥结构的平顶房,有宽两米的回廊,回廊上方3米高处是二楼上的走道,一个穿制服的人在上面盯着我看。我怯怯地望了他一眼后立即将视线转移开,生怕被他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来。真是不做贼也心虚。
我站在四方形院那几十秒钟的时间里,还看到四周的铁门上写有从1#……20#的序号、有20把两公斤重的铁锁在门上,有20个15厘米见方的关闭着的小洞(根据我在西域城监狱的经验这一定是送饭口了)、二楼走道上的四周有20块小黑板,上书有重刑犯姓名和囚室里的人数,黑板边上有向内凹进去的铁栅栏窗户。
没等我细细看完,我被叫到写有“3#”序号的门前,开门、“咣当”一声把我关了进去。
我这是进的第三道铁门。门里一步远便是一个占整个房间90%以上的地台,地台高约20厘米,约有十多平米的方形,一样是水泥的边沿,上铺木板。这是我以后长达几个月的“餐桌、床铺、座椅、走动的路……。”
地台上面左一堆右一群的人在玩扑克、发愣或聊天,大部分人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玩扑克的玩得都很认真,就如下了很大的赌注似的。
只有一个孤独的囚,安静地坐着。用她美丽而深藏着惊恐的眼睛看了我一会,当我看她时,她立刻将眼睛移向自己的脚尖。我无法想象有着这样一张高贵脸的年轻女子也是一个“犯人”。她就是芝子。
我开始体验贾队长的那句:“什么人到了我们那儿都乖乖的。”
门边一个臭气熏天、装满大小便的马桶。马桶紧挨着关闭着的风门,从门上的铁栏杆看进去可看到里面的毛坑和自来水管。后来我知道这个风门一天只开两次,每次十多分钟。我抬头再看上边的天花板,它高约六米,在东西两面约5米高的墙上各有一铁栅栏窗户,从东面的窗户看出去是铁丝网和另一个炮楼。我想这下可是插翅难飞了。
5
在我进去的前一天,从这窗口飞出去一个戴着枷锁的灵魂,它也带走了号子里另一些人的魂魄。那几个自知罪孽深重的囚,这会儿都抬头愣晃晃地望着那窗外。手中拿着这死去了肉体的人的遗物。
那两个被棉被盖着当梭梭板坐的老年妇人,被芝子和小蔓用水一滴一滴地救活了过来后,又为了她们所说的“信仰”,用绝食的方法予以捍卫,最后就死于她的“捍卫”。一起捍卫的另一个幸存的囚,就变成了一个唠叨的老太婆。
从我迈进门的那一刻起,老太婆就从地台子上爬过来,挨近我,叙叙叨叨地说:
“你一定要小心啦,小心啦。”
“小心什么?”
“小心人。”
“人怎么了?”
“人是糊涂的,就作恶事。”
“什么样的恶事?”
“杀人。”
“哦……。”
我被赦住了。老太婆笑了起来,头摇得像个拔浪鼓。两只手拍了拍,当两手要相碰时,却错了过去,并没有发出击掌声来。接着老太婆突然变了严肃而神秘的脸来,说:
“师傅已经超渡了。她现在已完全进入了美妙的境界。这些可怜的凡人啊,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罪孽之中,是在无边的苦海之中。你是新人,还可造就,一定要早早入‘世’。”
“什么样的‘世’?”
“那是一种法力;一种轻松的死亡。要好几年的虔心苦练,深入精髓,方能得道。”
我用一脸的迷惘对了老太婆。老太婆却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说:
“慢慢来,慢慢来。”
说完两脚一盘,在大腿和膝盖处,将两只脚底板交叉着翻在上面。这是一个高难的姿势,一般没练过功夫或体操舞蹈类的人是做不好的。我惊诧地看着老太婆,这时老太婆的两只手慢慢地,柔韧地平抬了起来,还是像蝴蝶。两眼闭着,进入了某种我不知道的状态。
查看984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