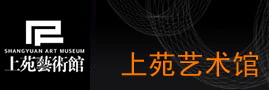|
超越审美之维——尹吉男访谈
时间:2002年7月25日
地点:中央美院办公室
(以下尹吉男简称“尹”,采访记者杨乐简称“杨”)
杨:您好,首先问您第一个问题。现在外面称呼您的说法特别多,比如说鉴定家、批评家、文化史学者或艺术史家,那么您对自己的哪种身份更为认同?
尹:其实我还是更认同文化史学者这样的身份,而且他是不管研究古代还是当代,都要具备当代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文化史学者,他的研究和思考都要和当代的文化、生活发生一种关联。但从个人兴趣来讲,我是比较喜欢视觉艺术的,对图像的东西更有兴趣。
杨:也就是说在文化史中更偏重于图像研究。
尹:对,因为这方面研究的人少,很多都是通过文字到文字来研究文化史,比如说都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从历史文献的记录上来讲,但图像的功能和文字有的时候有相似的作用,图像也记录历史,图像也记录思想,有时候也包含一些哲学,它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图像研究还是蛮重要的。
杨:以前看过您写的《绝非野生动物的文化眼光》等文章,觉得您的美术史研究更多地还是带有文化史角度的观察。
尹:是这样的,我尽了很多努力要超越风格样式或艺术性等单纯的审美视角,比如我讨论性别的观念、地域的变化,关注少数民族的问题以及比较明确地引入口述史方法,这些都是以往的美术史没有系统深入讨论过的,我在尝试用新的方法和视角来做。
杨:您原来学的是考古,那么后来怎么又想到学书画鉴定了呢?或者说您是怎样介入美术史的?
尹:一是对历史有兴趣,另外刚才说我是对图像更感兴趣,考古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考古要从地里挖出实物来,是有图像的,然后再对这个形象进行解释或去纠正历史,而纯历史都是要通过文献的,它不是,它文献也要读,也需要去看视觉东西。考古是一个大的时间概念而不是一个小的时间概念,比如说当代美术史还是个小概念,跟考古一比的话,一差万年。在考古这个大概念里边,它涉及的方方面面也不仅是跟人有关的,不仅包括人创造的文化,也包括自然,比如古代的气候、地理的条件、植被的情况或者当时的动物群,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但这些东西都是有形象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猛犸象的化石,或者一个恐龙的化石,或者古代的某种植物、鱼、河流,它都是在再现一个环境而不是仅仅读文献,我是对于仅仅读文献兴趣就会小一些,但如果把文献和图象互读兴趣就比较大。当时报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原因也和这有关,但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在学习当中就会对跟人相关的部分更感兴趣,因为它更加复杂,与人的精神动活联系得更紧密。比方说一种植物,当然从古今来讲它有变化,但这变化还是相对的,可是从艺术品的角度讲人自己做的东西变化太大了。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相比当然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的变化非常大,所以对它就容易有一种兴趣。在考古学里,确定一个物质文化或有形文化的时间性是第一要义,首先确定是什么时间,然后再展开讨论为什么它在这个时间而不在另外一个时间里发生,它有时间的问题。但有一点,在早期历史里,特别是在唐以前,考古会显得很重要,有形文化、视觉文化、图象文化都可以通过考古解决时间性问题,但从唐以后,特别是宋元明清,艺术史发展到最高最复杂的部分事实上就是书画,尤其是后期,它比别的要复杂,它的精神性的活动更多,所以有些西方学者也讲过,说中国绘画实际上是哲学家的绘画而不是艺术家的绘画。但这些作品都不是出土的,都是传世的,这就遇到一个年代性的问题:怎么来确定这一部分的年代序列?当时我有个野心,要对整个中国的视觉文化史有一个观察,北京大学解决了前半部分但解决不了后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在北大不属于考古的范畴而属于文物的范畴。考古是通过挖掘、清理,最后得到年代上的标志,而文物是传世的,通过官家或私人收藏,它找不到考古学上的年代序列,这事实上是问题最多的,但我对它有兴趣,因为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高深的学问,只有很少人能够掌握。后来就到美术学院读研究生,学文物鉴定,当时我的导师是金维诺教授和杨仁凯两位先生(校内和校外),由杨先生介绍我就跟着鉴定组全国各地的看了五、六万件东西,那时一般都是上午看东西,下午开讨论会,因此从广义上讲很多先生都是我的导师。
杨:从开始到现在,您的学术肯定在不断发展,那么我想请您谈谈影响您学术进展的几个问题。
尹:在北京大学时虽然没学美术史,但对考古品中的美术品特别感兴趣,比如壁画、画像石画像砖、还有陶俑。
杨:那是因为好看吗?
尹:我一直是对比较复杂的东西有兴趣。当时我在毕业那年有个实习,我们这一组是关于汉代,针对汉画像石墓和一些地面遗存的石祠堂进行了大概半年时间的考察,把整个山东苏北地区都跑遍了,看了大量东西,带队的是俞伟超先生的研究生信立祥,他的研究方向就是画像石。我们四个人主要考察的是孝堂山郭氏石祠,主要工作是对这个石祠堂的建筑做重新测绘,另外还要把它里面的图像缩小五分之一再描画下来,当时的分工是这样,信立祥和一个同学负责建筑测绘,冯石负责整理题刻、题记,我呢则负责把图象在打成方格的纸上按比例画出线图。后来我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画像石的,由俞伟超先生指导,题目是《东汉石祠的建筑形制和画像的基本组合》。从这个研究里我开始注意一个问题,即功能,以前人们不太注意,把许多东西都天然地看成艺术品,事实上它们原来并不是艺术品,这里面有一个功能变迁的问题。我那时的兴趣就在功能变迁上,怎么一个东西原来不是艺术品的就变成艺术品了,要经过那些历史过程。还有就是当时我提出要把画像石放在完整的空间里释读,不能单独来看。有画像石的地方可以做一个区分,一共三个地方:地面的祠堂、墓园大门口的石阙、、地下的墓室,这三个地方有三种功能,不能混在一块儿阅读,意思都是不一样的。另外还要考虑每一个墓之间是怎么组合的,每个墓的不同位置上的内容又有什么样不同的目的,比如说左壁、右壁、山墙、隔梁都要做细致的区分。这样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后,就可以把比如象傅昔华编的《汉代画像全集》这样零散的资料分出来,那些是墓室的,那些是祠堂的,它应该是哪个部位的。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来阅读图象,然后再研究他们的组合关系,那是我当时的兴趣。
杨:我知道国外一些学者很早的时候就在带着他们的研究生试图复原一些零散画像石的位置,您当时有没有受到他们影响呢?
尹:主要还是自己想到的。因为国内那时侯解释画像石主要是解决图象与汉代生产、社会生活的关系,比如用什么样的农具呀、穿什么样的衣服呀、坐什么样的车呀,基本上是作为历史的印证而忽略观念化的东西,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观念,但它是很观念化的,它这么做总要考虑干什么用,它不是仅仅为了把现实生活保留在地下,保留在鬼神世界,它比较复杂,我觉得。墓室是阴间的世界,陵园则涉及到守卫,它是一整套的观念系统,只有放到这个大的范围里来,才能破解画像石的含义。
当时只是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后来到中央美院又开始学习书画鉴定,我学的主要是"目鉴"。那时候我的最大的问题是关于风格,风格的概念和风格方法的运用。这个问题的突破点在于后来淮安明代王镇墓出土的二十五张画。鉴定组的杨仁恺、傅熹年等先生都说这个墓挺有意思,劝我关注一下,我也觉得每一次的考古发掘都应该对研究有所推动,等于说是个机会,于是我就对这个墓进行了实地考察,看了发掘报告等许多东西。那么这批东西究竟对研究有什么推动呢?就是关于风格的概念。以往我们说时代风格是有许多问题的,深究起来我们讲的时代风格都是个别画家的个别作品的风格,比如谈北宋风格无非就是李成、范宽、郭熙、许道宁、燕文贵,而且也不是指他们所有的作品,只是那么一件两件,也就是说我们把主流画家的主流作品的风格当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格,这等于偷换概念。这是没有概率的。时代风格应该是统一性的、共性的东西,但一个画家的共性是什么呢?他的作品从早到晚是怎么变化的?不同题材是怎么变化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资料很少。所以用这些作品来鉴定一个时代的风格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后来我就在淮安墓那个研究里最早把时代风格的概念分为两个,一个叫主体时代风格,还有一个是非主体时代风格,特别提出在鉴定学当中要加强对非主体时代风格的研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非主体时代风格这样的标尺,也就无法鉴定非主体时代风格这样的作品。淮安的材料是一批有明确记载的明代早期代表性的画院体浙派画风的艺术家,比如李在、谢环,但他们在这儿出土的画却不是院体浙派画风,而是带有"文人墨戏"的东西,这批作品如果不是出土的话,肯定会被当代鉴定家认为是假画,因为他们不熟悉这样的画风,所以这等于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即使同一个画家他也会有多种面貌,他有一部分作品可能是归入时代风格的,而有一部分可能没有归入,但这些作品仍然是真的要对鉴定的复杂性进行研究,个人有个人的主体和非主体,时代有时代的主体和非主体,各种风格都引入的话我们才能建立标尺,如果标尺本身就很贫乏,那么丰富的作品是没办法讨论的。王镇墓是说明这个问题最好的例证,事实上我是拿它来向已有的鉴定观念进行提问的。
接下来我又关心真伪观的问题。通过研究发现真伪观其实并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我把它们称为考古学的真伪观和艺术史的真伪观。考古学的真伪观是有绝对性的,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它只有一个答案,是还是不是,艺术史的真伪观则与考古学的真伪观既有重合又有区别,比如从一个个别作品的真实性来讲它绝对不是六朝的,六朝的书画作品传世的事实上一件都没有,最多就是唐和宋的摹本,从真实性的角度来讲绝对真实就不存在了,被瓦解掉了,但有一点,尽管有些作品从绝对性来讲不是那个时代的,但却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样式。比如一些宋人模唐人的画,它的时代是宋不是唐,但它的样式是唐不是宋,有这样一个矛盾性。因此美术史的真伪观要比考古学的真伪观要宽容一些,要允许样式的真实性,就是作品的真实性被否定了,但作为样式的有效性仍然存在。我们现在研究很多作品,特别是唐和六朝,都是根据摹本来进行研究的。鉴定学的研究要对这两种真伪观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做个别的研究,要让它们来互补,从而建构一个完整的时代风格。
又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在想近现代鉴定家脑子中的标尺是从哪儿来的。逐渐地这个问题得到清晰化了,对近现代鉴定家来讲,在美术品的断代特别是绘画的鉴定标准方面,他们共同的老师还是明末清初的一批鉴藏家,因为他们都写了著录书,他们著录过的书画作品在世界各博物馆都能看到。接着我就考虑他们的标准是从哪儿来的,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是我的一个新的兴趣,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明清鉴定家的晋唐画概念》(发表在《文物》2002年第7期),专门讨论明末清初的鉴定家有没有鉴定从六朝到唐朝的绘画的能力。回答是相对否定的,我认为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对宋元画的命中率和准确率比较高,对晋唐其实是错误百出。但他们对现当代鉴定家影响很大。去年我参加大英博物馆顾恺之讨论会写了一篇新的文章:《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讨论这些明代后期鉴藏家是通过哪些渠道获得六朝绘画知识的,比如从出版上他们能看到哪些书,从流传上他们能看到哪些画,书画家之间有哪些交往,另外这些知识是否有效,通过我的考察,比如说董其昌的六朝绘画知识差不多是白痴状态,知道的很少,这当然是有比较的,跟他知道的关于六朝书法的知识相比,相差得非常悬殊。他对六朝书法特别是碑帖的了解非常厉害,比如对王献之《大令十三行》的流传情况就相当清楚但对顾恺之的了解就出不了那几个文本。这个文章是有一个很大推进的,不光对鉴定,对艺术史也是这样。在这篇文章里我想用新的方法提一个重要的问题,文章的副标题就叫做"以顾恺之的概念为线索",英文翻译的特别好,"Tracing the Concept of Gukaizhi"。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到顾恺之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概念,或进一步讲顾恺之实际上是一个概念人,我们说的顾恺之是当代的,不是古代的,因为这个人已经被历史合成了,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谁也不能证明现在说的顾恺之是东晋那个人。我是拿顾恺之作例子来考察一个历史人物是怎么一步步生产出来的。最后结论很清楚,事实上是有六个顾恺之。在那次会上我也开玩笑,说"我们这个会呀最应该来的就是顾恺之,可顾恺之不是一个是很多,那么到底给谁发签证呢?都来的话他们之间认不认识?"这是个问题,因为他们产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六个顾恺之呢?有三个是文本的顾恺之,有三个是作品的顾恺之,这是两类不同的顾恺之,作品的顾恺之晚,在两宋时代完成,文本的顾恺之早,但也没有早到东晋,最早的文本是南朝刘宋时期都是刘义庆写的《世说新语》,他是第一个生产顾恺之的人,在《世说新语》里有十几个碎片是关于顾恺之的不同记载,但这个顾恺之不是美术史意义上的顾恺之,他是文学意义上的顾恺之,说这个人很有趣,有三绝,会妙语连珠,都是文学化的。而且这个文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顾恺之呢?这都很难说,因为我们没有东晋的记载,没法比较,反正我们知道第一个关于顾恺之的记载就是这样的,我们只能知道谁说但不知道说的是谁。第二个顾恺之是到了初唐的房玄龄等文臣受唐太宗之命写《晋书》,这里有第一个系统的顾恺之的传记,但是把他作为一个正史人物来写的,因此也不是美术史意义上的顾恺之,两个文本之间有部分重合,但也不完全重合,刘义庆时代知道的很少,房玄龄时候就知道很多了,那么他凭什么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提到文献,但我们知道他的生产期是在初唐。第三个顾恺之才是和美术史有关的,就是到了中晚唐张彦远写的《历代名画记》,在这个顾恺之里提出了三个重要概念,一是顾恺之是传神论的理论家,第二他是宗教题材的壁画家,第三他是画丰富人物题材的卷轴画家,现在来看这三个概念中有一个塌陷了,就是宗教题材的壁画家,因为我们看不到一件作品,这些寺庙都被毁掉了,另外两个概念中作为传神论理论家虽然可以看到只言片语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而卷轴画问题就更复杂了。但不管怎么说,文本的顾恺之在中晚唐时期已经全部完成,我们现在,包括董其昌的时代所能看到的文本都超不过这些。另外三个是卷轴画的顾恺之,也叫艺术品的顾恺之,我们知道的《洛神赋》、《女史箴》、《列女传》三幅作品都纷纷跟顾恺之建立关联,通过知识考古,我们发现建立关联的时期都是在北宋到南宋之间完成,但我不是说这些作品就是宋代的,而是说从宋代起人们开始说这些画是顾恺之画的。现在六个顾恺之都出场了,那么什么时候合成?就是在晚明,这其中鉴藏家起了重要作用。合成的顾恺之再加上晚明清初人对他的评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顾恺之。在大英博物馆时我也开玩笑,其实这个合成的顾恺之他什么都没干过,也没画过画,也没说过话,他只是"顾恺之"。当时论文宣读后很多与会学者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认为这是用一种特别新的方法说明一类具有普示性的历史问题,比如说董源、吴道子,书法上的二王,也包括文学上的大谢小谢、陶渊明、李杜,他们都有类似性,他们的神话都有一个逐步的合成过程,而这些过程都有效地建构了我们现在的知识,我们不能知道这些知识是否合法但却无法逃脱它们。因此我们必须要先对已有的知识一项一项进行清理,它是怎么来的?是否有效?可不可用?这就是我的文化史兴趣,它不仅是考虑视觉的问题。另外现今的文化史又要关注当代,你的问题是要有当代性的。我的兴趣从来都不是将古代的东西还原,还原只是手段之一,要通过还原对当代人的思想发生作用,要对当代鉴定学,对当代艺术史观、文化史观有所触动,要具有反思性。
此外我还有一个领域是在现当代,我一直比较关注现代,特别是近20年的艺术家是怎么塑造中国形象的。2000年的时候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做过系列演讲,分为不同的主题,比如女英雄形象的生产,国粹观念的转化,领袖像等等,这也就是我现在写的一本书,叫《中国形象》,讨论20世纪中国艺术家是怎样建立中国概念的。以前人们总以为我是做当代评论的,评论是比较感性化的东西,其实我也做研究,比如做过20世纪女性史研究,从2000年开始又做大部头的当代中国口述美术史。
杨:可以看出您一直保持着比较清晰的思路。那么在学术进展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东西让您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呢?
尹:我是从传统鉴定学入手的,花费很多年学会了"目鉴"的方法,但我现在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对传统的方法进行不断的挑战、提问、解构,这当中就有很大的矛盾性。巫鸿曾经问我最想写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能够鉴定吗?"我们都笑。这其实是人类的普遍行为,我们永远都面对辨别真伪的问题,不光是艺术品了,还有人、事件。
杨:这等于说我们能够判断吗?
尹:事实上就是方法的有效性问题。目鉴是有效的,可总会有冤假错案,那么你又怎么证明你的判断不是冤假错案呢?到底以什么样的牺牲作代价才能建构起一个学问,就像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死亡率为代价才能建立起现代交通秩序?没有一种方法是全能的,每一种方法都会带来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当年兴致勃勃地到美院学习鉴定,以为学会以后就可以进行目鉴了,其实真正学会了以后才发现问题很多。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困惑我一个人的问题,可以说它是个很大的哲学问题,可能我们花很多时间也解决不了。但在努力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就会对人类的思想有意义。我觉得人类就是这样,很多人都是在努力解决一个终极问题,最后还是没解决,甚至显得很荒诞,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新的知识系统产生了,这就会使人觉得好像没有白过吧,否则的话你会极度的心理不平衡。
杨:刚才您谈到您的兴趣领域很广,从古代书画鉴定到现当代研究评论,等于说您做研究面对的是古代和现代两个课题,它们的工作量都相当庞大而且艰巨,但您又不能放弃任何其一,都得一点点做它们。
尹:虽然是两种问题但它们之间有一个共通性,可以互相贯通。在当代可以发现问题,在古代可以找到一些更加丰富的资源,问题和资源互补。如果光是研究古代,你的问题就可能并不敏锐、不清晰,和当代思想的关系不明确,但在当代历史中发现了问题,如果能有一个长线的观察,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会更深入。这样做确实比较累,实际上做一个专业是最简单的,而且最有效,比如成为一个唐史专家、近代史专家或当代评论专家,这都是相对来讲要容易些。我也是考虑我的战线太长,每一个战线都要消耗你很多的精力,这样做东西进展就比较慢,但我觉得如果能有一点推进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标志着往前走了一步,所以尽管慢但还是有很多好处。而且我知道西方一些学者走的也是这条长线。
杨:对,比如汤因比,他一边写十卷本的《历史研究》,一边与妻子一起编写“两战”时期的年鉴,都是很辛苦的工作,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另外,我也觉得您不同于一般概念里的书斋学者,因为您好像很早就介入了电视和其它现代媒体,这就涉及到学者与大众接触的问题。
尹:一方面媒体是一种视觉传达的手段,它可以把你的理念、思考、知识传达出去。另一方面,它也能增加我的触觉。媒体一般有很高的制作费,这样就可以给我提供很多方便和资料,比如做女性史时就专门配有有四、五个人帮我查阅资料,并提供我机会到电影厂看大量二、三十年代的老电影,到新影厂看外国人拍的老记录片,还为我找来其它需要的旧杂志和专著,资料会增加对问题的感受和深度,但这些事情如果全由我一个人来做那十年也做不完,可这样两年就完成了。另外我经常说进入媒体等于是用另一支笔写作,用电视这支笔来写文化史,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尝试,特别是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它里面有许多鲜活的史料,保留了许多珍贵的不可再生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可以说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知识。事实上我是希望能利用媒体做一些学术性的思考、理念推进和视觉传达。除《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外,其它我还做过《点击黄河》、《发现曾侯乙墓》、《滇越铁路》、《珠峰登山史》,还有关于京津解放的平民回忆史等。电视媒体有图象、声音等多种表现手段,是钢笔和电脑所取代不了的。
杨:那您对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打算?是否会把它们贯穿在教学中?
尹:我希望在下一阶段继续用文化的眼光、社会学的眼光来扩大视觉文化。而且在美术史系课程的设置上我也想尽量增加一些考古、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让它们在保留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多元化。研究生方向也会逐年扩大,比如明年我和贺西林要带的课题是"中国美术考古学",意图从美术史角度来看考古品而不是从考古学的观念来看美术品,另外还要增加"视觉文化和性别观念研究",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不能做所有的事,但可以指导一些人去做,这样逐渐地就会为多个领域带来很多专家。
杨: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您对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看法。
尹:对当代美术史研究来说是评论太强大而问题的研究少,包括我本人也做一些评论,但评论最终还是凭直觉,是带有经验性反应性的,无法给学问带来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研究。比如巫鸿,他不做评论,只做研究,当然也包括资料的整理,文献的收集。对传统美术史研究来说呢是材料性研究多而问题性研究少,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材料专家,对知识背景很熟悉,但整体来讲还是跟发达国家的研究有一些距离。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新的而不是一般性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要有挑战性,要能开阔新的思路。总之史和论是不应该分开的,理论不是为了纯粹的推理,治史也要针对问题。 |